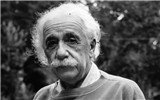[摘要]《唐宋词名家论稿》分别论述了温庭筠、韦庄、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等十六位名家的词作,既揭示各家词作的精微品质、在词史中的地位,又寻绎其间纵横交织的联系与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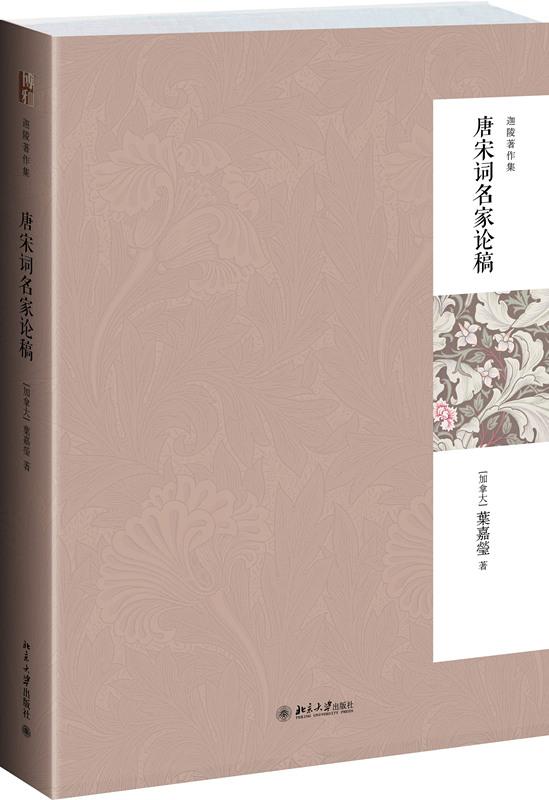
《唐宋词名家论稿》,叶嘉莹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摘自《唐宋词名家论稿》,叶嘉莹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一
临川珠玉继阳春,更拓词中意境新。
思致融情传好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昔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曾称:“《阳春》一集为临川《珠玉》所宗。”前论冯延巳词时,亦曾引刘攽《中山诗话》之语,云:“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而冯词最值得注意之成就,盖在其词中意蕴之深厚,可以引起读者极丰富之感兴与联想,晏殊词之成就,亦颇有近于是者。昔王国维《人间词话》即曾称冯词《鹊踏枝》之“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数句,以为有“诗人忧世”之意;又曾称晏词《蝶恋花》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数句,以为有合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夫冯、晏二词之所写者,自其表面观之,原亦不过为伤春、悲秋、念远、怀人之情思而已,然而却有足以引起读者较深远之联想者,私意以为其主要之原因,盖有以下数端:二人词作中之所叙写者,皆带有鲜明之主观感情,在叙写之口吻中,极富于感发之力量,此其一;二人对于所叙写之情事,又并不喜作直言确指的说明,故而易于使读者产生多方面之联想,此其二;二人之学识、志意及其在政治方面之经历,又皆足以在其内心酝酿为一种较深厚之意蕴,此其三。是则晏词与冯词在作者之本质方面,固早有相近之处,何况冯氏一度罢相出镇抚州有三年之久,而晏氏则正为抚州之临川人,其词风曾受有冯氏之影响,亦正有地理方面之因素在。故世之论词者,多谓晏词出于《阳春》,斯固然矣。然而凡文学艺术之创作,又多贵在其能于继承之外,别有开发。晏词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能在继承冯词之风格以外,更有属于一己之特色多端。
关于晏词之特色,如其闲雅之情调、旷达之怀抱,及其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诸点,固皆有可资称述者在(可参看拙著《迦陵论词丛稿》中《大晏词的欣赏》一文)。然而其最主要之一点特色,则当推其情中有思之意境。盖词之为体,要眇宜修,适于言情,而不适于说理,故一般词作往往多以抒情为主,其能以词之形式叙写理性之思致者极为罕见。而晏殊却独能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中,在伤春怨别之情绪内,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的观照。如其《浣溪沙》词之“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及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诸句,便都可以为此一类作品之代表。前者在认知了“念远”与“伤春”之徒然无益以后,乃表现出“不如怜取眼前人”之面对现实的把握;后者在对于“花落”之“无可奈何”的哀悼以外,也表现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一种圆融的观照,遂使得这两句词在“自其变者而观之”的哀感以外,也隐然有着“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一种哲思的体悟。这实在是晏殊词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特美。
如果以晏词与冯延巳词相比较,则二人之词,固皆足以于其表面所叙写之情事外,更使读者体悟出一种感发之深意。然而其所以使人感发之本质,则实在又并不尽同。冯词是以其盘旋郁结的深挚之情取胜,而晏词则别有一种理性清明之致。即如冯词《鹊踏枝》之写情,则有“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之语,其叙写之口吻,如“每到”“依旧”“日日”“常”“不辞”等字样,其所表现之感情,皆极为热烈执著,有殉身无悔之意;至于晏词,则如其《浣溪沙》之“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二句,其叙写之口吻,在上一句之“空”字与下一句之“更”字的呼应之间,则表现了虽在伤感中,也仍然具有一种反省节制的理性,因为其下句之“更”字所写的虽是“念远”更加上“伤春”的双重哀感的结合,但其前一句之“空”字,则是对于“念远”及“伤春”之并属徒然无益的理性之认知,于是遂以第三句之“不如怜取眼前人”作了一种极为现实的处理与安排。再如其另一首《浣溪沙》词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则在伤春之哀悼中,却隐含了对于消逝无常与循环不已之两种宇宙现象的对比的观照。像这种富于理性与思致的词句,在一般词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而晏殊则不仅能将理性与思致写入词中,而且更能将理性和思致与词之“要眇宜修”的特质作了完美的结合,使其词之风格,在圆融莹澈之观照中,别有一种温柔凄婉之致。晏殊词集以《珠玉》题名,这与他的词珠圆玉润的品质和风格是十分切合的。
二
诗人何必命终穷,节物移人语自工。
细草愁烟花怯露,金风叶叶坠梧桐。一般说来,在中国文学之传统中,常流行有一种“文章憎命达”及“诗穷而后工”的观念,早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就曾经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话。此种说法原有相当之真实性。我在《〈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一文中(见《迦陵论词丛稿》),便曾谈到“由外物而引发一种内心情志上的感动作用,在中国说诗的传统中,一向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基本要素”。至于可以引起内心之感动的外物,则大约可以分为两种来源,其中之一种即为人事方面的感动。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生活上所遭遇的挫伤忧患,常可以使诗人在心灵中受到一种感发刺激,因而写出深挚动人的诗篇,这其间自然有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在,所以“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论。
而如果持这种观念来衡量晏殊之词,则晏殊之富贵显达之身世,却既不能满足读者对诗人之“穷”的预期,也不能使读者因诗人之“穷”而获致一种刺激和同情的快感。因此一般读者对于晏殊之词都往往不甚予以重视。然而晏殊的词作中,却实在极富于诗歌感发的质素。盖以诗人自外物所获得的感发,除去源于人事界者以外,原来还可以有源于自然界的一种感发。钟嵘的《诗品序》,对此更是在一开端便有所叙及,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后又引申其义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而早在钟嵘《诗品》以前,陆机之《文赋》便亦曾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之言。可见对于一个真正具有灵心锐感的诗人,纵使没有人事上困穷不幸之遭遇的刺激,而当四时节序推移之际,便也自然可以引起内心中一种鲜锐的感动,而写出富于诗意之感发的优美的诗篇。
而晏殊便正是禀赋有此种资质的一位出色的诗人。如其《踏莎行》词之“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及“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等句,便都写的是对自然界景色节物的敏锐而纤细的感受,而此种敏感往往又可以触引起诗人一种深蕴的柔情,故前一首之后半阕,便写有“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之语,而后一首在后面也曾写有“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之语,都表现了由锐感所触引起的一种缠绵深蕴的柔情。再如其《清平乐》词:“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则较之前二词所透露之感情更少,几乎全首都是写对于节物气候的锐感,仅在结尾一句之“银屏昨夜微寒”的叙写中,隐约表现出一种凄寒怅惘之情而已。像这一类词,既没有悲慨奋发的内容,也没有激言烈响的气势,所以很不容易获得一般读者的赏爱,然而这一点凄寒怅惘之情却实在具有使人心动的感发。
古人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能引发读者一种多情锐感的诗心,这正是晏殊这一类词的可贵之处,颇近于王国维所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的境界。因为善感的诗心,才是一切好诗的基本根源之所在。而晏殊则正是把这种诗感表现得极为敏锐精微的一位作者,这是我们在欣赏晏殊词之时,所最不当加以忽略的。
(本文为腾讯文化独家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详细]
-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