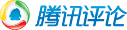[摘要]有人说起义基本成员是农民即可,可希特勒大军的主体也是工农。
原载《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
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经过多年的浸润与濡染,媒体或教材用语往往带有异样的价值色彩与爱憎倾向,“农民起义”一语就是如此。1979年出版的《辞海》里,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而在“维基百科”2009年收入的词条中,则将“农民起义”界定为“中立性、有争议”,并给出定义:“农民运动,又叫农民起义、农民起事、农民战争,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的……术语,通常意味着农村或农业人口的暴动,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可见,农民起义其实是一个不无异议、值得讨论的话题。
“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通史》第四章)是写入官方史书的。历史上的“民变”“暴乱”乃至“邪教”事件,曾几何时,在主流话语中,其主体变成了笼统的“农民”,其性质则变成了正义的“起义”。“起义”者,“仗义起兵”、“正义起事”也,正因如此,不少历史学家往往按这一观念加以诠释,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被诠释成一部农民起义史。如在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农民起义”出现了349次;在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中,“农民起义”出现了561次;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里,“农民起义”也出现了100次。
学术无禁区。作为学术研究,采用任何观点、任何视角都无可非议,但在史学研究中,预设结论、先定基调,然后照此搜集、填充、取舍、剪裁历史资料,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要,这不仅不是“以史为鉴”,反而是曲解历史。倘若再把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当作金科玉律,在历史问题上一锤定音,在学术问题上一言独尊,并以此要求学界与学者,同样不符合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如果人们能够摆脱极左思潮的羁绊,冷静面对尘封的历史文本,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加速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发挥了某些作用的话,那么,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实在看不出有太多的进步意义。
历史动力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一些人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加区分地一概定性为“历史动力”,但这种看法并不是通过历史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本文不拟从价值肯定的角度谈论农民起义,文中关于“起义”的文字,均为中性用语。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肯定有其社会客观因素,说明当时的政权或社会的确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或严重的危机。然而,解决这些矛盾、危机,起义并非唯一途径。起义作为一种代价高昂的社会变革,其实是不得已的政治选择。即使作出选择,也未必能达到社会预期。动机与效果、预期与结局、纲领与实践往往并不一致。笔者曾试图对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政治纲领与口号作出分析。由于这些纲领与口号只具象征性、暂时性、工具性,有的的确反映了民变群体的真实愿望,有的只是小生产者的经济政治空想,有的只是出于拉杆子、搭台子的工具目的,有的则在地位变化之后被自身所抛弃……原因种种,促使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
按照武断的“历史动力”理论,漫漫两千多年的中国史,似乎存在着一条历史射线,这条射线通常以秦代为起点,向前延伸、辐射着,经过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仍然没有终点。按照这种理论,射线之上的历史角色只有农民与地主,农民起义则是这条射线的动力源;射线之外,举凡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民族纠纷、文化科技、外交国防,统统不见了。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仅不会出现倒退或回潮,甚至不会出现上升中的螺旋,整个历史潮流似乎只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然而如果农民起义总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如果农民起义总在推动历史一往无前,且不说从“雄汉盛唐”到“弱宋腐明”的笼统说法,古代中国陷入皇权专制的长夜何以持续两千多年?近代中国何以屡屡陷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悲惨境地?
在我国,存在着两种传统的“历史动力”理论,一是“人民论”,一是“农民起义论”。但历史进程从来不会为哪杆旗帜下哪股势力所左右。恩格斯就曾严谨地论述了这一点。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每一个体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绝不限于“人民群众”或“农民起义”。恩格斯对历史动力问题进一步作出概括:“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活动,当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环境去考察。单纯地站在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对于确立俯瞰整个历史进程的历史观,都是偏颇的。如果政治人物基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古为今用,史为政用,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认为:“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这些举措,在中国历史上存续较长的王朝都可以看到其痕迹。而在那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一些民变头目那里,是很难找到的,这也是一些民变头目即使一时得逞甚至抢到政权也无法长久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当代史上,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可谓波澜壮阔,如何评价其得失与成败,邓小平曾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科学的。那么,农民起义是否历史动力,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跨度更大的历史活动和历史现象,显然也需要一套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潘旭澜先生在评论太平军时曾经指出:“如果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民族的团结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标准当然可以讨论,但笔者以为,这个标准大体是客观、科学的。潘旭澜先生曾对太平军的历史活动与历史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这场导致社会经济极大破坏、生命财产极大损失、传统文化极大摧残的所谓起义,不仅打乱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且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要知道,英法联军对我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包括火烧圆明园)、沙皇俄国逼迫清廷割让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都发生在太平军播乱东南半壁之中或之后。在这个意义上,太平军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不是什么历史动力。
此外,不知是否有人误用了对立统一理论,在任何事物中都要找出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才能证明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奴隶社会总要奴隶与奴隶主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社会总要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统一,封建社会当然要农民与地主对立统一。在这种理论支配下,我国的历史学变成了僵化的阶级斗争学说。
将我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简化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这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从根本上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不仅存在着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此等等。这些矛盾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着、变化着,有时此种矛盾处于主导地位,有时彼种矛盾处于主导地位。春秋时的百家争鸣、文景时的休养生息、两晋后的民族融合、贞观时的开明政治、开元时的文化开放、两宋时的政治宽容,这些历史事件或历史活动并不能一概归结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它们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显然不亚于农民起义。而战国时的合纵连横、三国时的金戈铁马、中唐时的藩镇争权、宋辽(宋金)间的百年战争、蒙元时的征服杀伐、明中期的宦官专政、康乾间的文网字狱、晚清时的甲午战争,它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可否认,且不论其作用之正负,至少不能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事物复杂的发展变化简单化、庸俗化,这是“文革”中常常出现的逻辑。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反观国内一些理论,将农民起义视为单一线索或“真正动力”,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这显然不同于恩格斯的“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
农民起义领袖并非农民
前年,笔者曾写过一篇《宋江一伙并非农民起义》(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文中对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职业出身作了初步分析。近日看到唐元鹏先生的《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一文。文中以中国历史上12次农民起义作为分析对象,依次是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军起义。据唐先生考证,这12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其职业可稽考者有35人,其中:
吏员9人:刘邦(亭长),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李自成(驿卒),徐天德(差役)。
商人8人:黄巢(盐商),王小波、李顺(茶贩),方腊(漆园主),钟相(小商人),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出身4人:陈胜、吴广(屯长),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贵族3人:项羽(没落贵族),刘秀(远支皇族),李密(蒲山郡公)。
地主2人:韦昌辉、石达开(小地主)。
宗教人士13人:张角(太平道),钟相(自封天大圣),方腊(明教),韩山童、徐寿辉、刘福通(白莲教),朱元璋(明教),徐天德、王聪儿(白莲教),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拜上帝会)。
农民3人:杨幺(相传为渔民),杨秀清、萧朝贵(烧炭农民)。
笔者对这一考察结果进行统计,得出如下结果: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曾为基层官吏、下层军人、商人或出身贵族、地主的有26人,占74.3%;与宗教有关或打着宗教旗号的13人,占37.1%,真正的农民只有3人,占8.57%。这一结果,与我前年对梁山一百单八将所作的职业分析基本吻合。
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仅仅考察其出身和职业,作为分析其社会立场与社会行为的基础与支点,似乎过于单薄或孤立;然而,这些多年被推崇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居然不是农民,确实与一般人的想象大相径庭。他们的社会行为既不反映农民意志,也不代表农民利益,如果将这样的社会行动称为“农民起义”,的确十分勉强。
有人或质疑说,农民起义的领袖并非纯粹的农民,但起义队伍的基本成员是由千百万农民构成的,因此,以其领袖的职业和出身来否定这个队伍的性质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质疑者忽视了事物的另一面,即起义者的敌人--官军,其基本队伍也是农民,而这并不意味着官军也是他们同一堑壕的战友。谁又能说希特勒百万大军的主体不是工人与农民?
农民起义的历史怪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古代中国的农民,既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不代表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模式,无法突破时代与自身的局限,只能在原有的经济与社会格局中制造一些冲突与波澜。每次农民起义的潮水退去,人们在历史的海滩上发现,中国社会仍在皇权专制的磨道里兜圈子。换句话说,农民起义根本不曾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只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内原地打转而已。
翻开史书,农民起义往往呈现这样一幅图景,他们或聚众起事,或落草山林,经过多年流窜征伐,浴血奋战,或者推翻了旧朝廷,或者重击了现政权,或者建立了新王朝。在鼓角争鸣、王旗变幻的风尘过后,神州大地仍然是封建皇权。元代张养浩笔下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历史图景的真实描绘。
鲁迅先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争椅子”理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完整考察鲁迅先生这段话,其实是一论述、二举例、三结论的“三段论”。他的结论是“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皇帝’也是如此)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在朝的、在野的;保位的、造反的;“现在的”统治阶级、“潜在的”统治阶级,颠来倒去,如此而已。鲁迅先生目光如炬,入木三分,寥寥数语,说透了一部中国史。中国古代那些农民起义的头头们,不管他们喊出的口号多动听,折腾的动静有多大,目的无非就是“争椅子”--龙椅。争到了“椅子”后,就像阿Q所做的“革命梦”:“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马克思在遥远的欧洲分析了洪秀全太平军的活动性质:“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马克思引用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话说,“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同上)马克思所说的“强盗”式破坏与鲁迅所说“寇盗式破坏”,可谓异曲而同工。
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们往往呈现以下几种结局:
一是打下了江山,做了皇帝。如汉代的刘邦、明代的朱元璋,在鼓角声里,在刀剑丛中,虽然他们争到“椅子”,建立了新王朝,在皇权专制的本质上,却是换汤不换药。
二是过了皇帝瘾,旋即败亡。如唐末的黄巢(大齐帝),明末的李自成(大顺帝)、张献忠(大西帝),太平军的洪秀全(天王)。革命尚未成功,称孤道寡已是“第一要务”,但立足未稳,旋即覆灭,成了历史的笑柄。黄巢与李自成所部,已经占领帝国首都,最后功败垂成。而张献忠、洪秀全,不是疯狂杀人,就是骄奢淫逸。对于这些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骄傲自满和缺乏经验,在政治变迁的关键阶段,暴露的正是其自身的胸襟与眼界,正是其破坏有余、建设无能的群体特征。
三是做了嫁衣裳,他人称帝。在民变风潮的冲击下,旧政权摇摇欲坠,到头来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胜利成果为他人所窃取。在民变蜂起、天下大乱的年代,往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不得志、有野心的官僚、贵族,利用他们的统治经验与政治基础火中取栗,农民起义适成为他们窃取政权之工具。新莽的刘秀、隋末的李渊,就是在绿林赤眉起义和隋末战乱中夺取政权的。
四是折腾三五年,一地鸡毛。在中国古代,邪教势力似乎非常猖獗,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会等。它们是披着宗教外衣,还是邪教蓄意闹事,也许兼而有之。这种势力基本上没有进步意义,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只会造成破坏或动荡。
一些农民起义同样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农民起义,不仅不是历史动力,它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甚至比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危害更甚。人们常说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其实,一些农民起义同样沉重打击了人民群众,在这点上,中外思想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鲁迅先生评论李自成,因怕已经吃饱肚皮的换成一群空着肚皮的:“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利害的。”(《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在官方史家笔下,黄巢是一个“高大全”的起义英雄。多年后,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人物,不仅需要新的史料,而且需要新的视角。黄巢有三个重要经历,在当代官方史书中未曾提及:
一是屠广州。唐僖宗乾符六年(879)九月,因唐王朝拒绝了他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黄巢遂率军攻占广州,野蛮劫掠与屠杀。据梁启超转引:“回历纪元264年(相当于公元878年,与中国纪年有误差),叛贼黄巢陷广府(广州),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饮冰室专集》)这一史实在另一书中也得到证实,“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二是祸长安。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率军攻占首都长安,迫不及待地建国称帝。有人在大门上涂诗嘲弄黄巢军,黄巢部下竟将该衙官员和门卫全部挖去眼睛,头足倒悬,挂于门前;又在全城搜捕能写诗者并全部杀害;凡识字者均罚作贱役,所杀总计三千余人。(《资治通鉴》)中和元年(881年),唐军一度攻入长安,百姓协助官军将黄巢驱逐出城。黄巢再次攻进长安后,“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这座周、秦、汉以来的千年古都、世界名城,一炬成灰,从此再与首都无缘。
三是吃人肉。中和三年(883年)五月始,黄巢率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县)百日,粮食短缺,就制作了数百个巨型石臼,饿急之时,将大批乡民、俘虏,不分男女老幼,活生生扔进臼中,“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旧唐书》)。黄巢所过之处,人烟绝灭,赤地千里。这些史料经过后晋、北宋三个不同的作者群体,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均有记载。
唐末著名诗人韦庄的《秦妇吟》,在历史上,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并称“乐府三绝”。这首乐府以目击者的口吻揭露了黄巢所部在长安的弥天大罪:“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六军门外倚殭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然而对此,我们的一些史家在赞赏杜甫的“三吏三别”,肯定白居易《卖炭翁》的同时,却指责《秦妇吟》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污蔑。
另一个例子是张献忠屠川祸延百年。如果以历史动力的标准考察张献忠的所谓农民起义,可说是极大讽刺。在史家眼中,浩劫之后的四川是怎样的图景?“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死人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之,遍体皆生毛。”(《明史》)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使“天府之国”沦为“人间地狱”,以致自清康熙年间始,不得不实施长达百年的大规模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这就是史书为什么会记下“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寓之人”(《清史稿》)的根本原因。
《鲁迅全集》中有10多处谴责张献忠屠川的内容。有人对鲁迅先生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表示不解,而这恰好体现了这位思想家的远见卓识。鲁迅先生在《记谈话》中指出:“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这也就是孙可望所说的“有王无民,何以为国?”鲁迅先生批评张献忠破坏了“奴隶规则”,“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坟·灯下漫笔》)鲁迅先生谴责道,“张献忠杀人如草”,“为杀人而杀人”,“‘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柏杨在其史著中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历朝历代的中国百姓,无论面对在朝的执政者,还是面对在野的觊觎者,这些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动辄被屠城、大规模杀害;军队粮草不足时,竟把百姓活躯当作军粮;还有的绑架百姓到大街上屠杀切割,零卖人肉,政治如同刀俎,百姓形同鱼肉……史不绝书的太多苦难,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然而,一些所谓“专家”“学者”,仍将黄巢、张献忠这类杀人如麻的屠夫,将洪秀全这样严重戕害中华文化、招致深重外患的民族罪人,将李自成这种利欲熏心、鼠目寸光的野心家,通通奉之为“农民起义”,奉之为“历史动力”,奉之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往往以马列、鲁迅信徒自居,动辄把自己的学说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然而,对于马克思严厉谴责的太平军的倒行逆施,对于鲁迅反复鞭挞的张献忠的兽行,他们却充耳不闻。这不能不令笔者感叹:我们的历史惰性、历史因袭竟是如此深重!